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法律评论
公众关注的跨省办案,检方提出的证据不足,都不是鸿茅药酒案的核心问题。本案的关键点,一是在实体法上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二是在程序法上违反了比例原则。
在事实层面,如果商家捏造事实虚假宣传,有虚假广告罪;如果个人捏造事实虚假陈述,有损害商誉罪。但是,在商品价值层面,既然社会能够容忍一定程度的广告浮夸,商家就也得容忍公众的批评贬损。面对名誉权与言论自由之间的权利冲突,这里体现了一个精致的对等设计。
阅读要点:
第一,警方跨省办案并无不当,不存在滥权的问题。
第二,“跨省抓捕”的问题不在于跨省,而在于捕后羁押,违反了比例原则。
第三,将价值贬损的行为类推适用损害商誉罪,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
第四,检方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退回补充侦查,处置方式存疑。
第五,彩蛋:为什么损害商誉罪不禁止价值贬损?
鸿茅药酒案的曝光已有些时日了,网上的各种评论铺天盖地。不过,看过之后,还是觉得应当得到重点强调的,似乎还没有被特别突出,相反,一些枝节或发散性的议论,又有些被过度渲染了。
这样一种弥散的状况,导致问题有些失焦。而这个影响性案件中蕴含的反思性能量,以及对以后类似案件有启发和借鉴的法律关节,可能也容易被遗憾地淡化了。
开门见山地说,鸿茅药酒案的问题,与跨省办案或证据不足无关,而在于违反罪刑法定与比例原则。
第一,警方跨省办案并无不当,不存在滥权的问题
多家媒体使用了“跨省抓铺”这样的表述,甚至有媒体使用“穿越大半个中国来抓你”的标题。但是,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警察跨省办案,当然有法律上的根据。这里就不摘引了。
实践中,跨省抓捕是很多刑事案件的办案常态,甚至,有时候会成为警方侦破一些大案要案的必经手段和正面宣传。所以,“跨省”这样一个法律上没有疑问更谈不上滥权的做法,显然不是鸿茅药酒案的核心问题。
当然,用标题党来吸引公众,就和警方经常跨省办案一样,也是媒体常用的手段。普通老百姓一看“跨省”,立感不安,被吸引进来关注这个案件,最后形成了舆论倒逼的力量,客观上也是好事。
不过,关注之后,就没有必要总围绕着“跨省”打转说事儿了。
第二,“跨省抓捕”的问题不在于跨省,而在于捕后羁押,违反了比例原则
根据公开报道,谭秦东被内蒙古凉城警方跨省抓捕后执行拘留,后经检察院批准,以损害商誉罪被执行逮捕。如今回头来看,就刑事强制措施的适应性和相当性而言,逮捕的决定是否正确,恐怕存有疑问。
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这五种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的强制措施,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强度,是由低到高的。强制措施如双刃之剑,适用时必须受到比例原则的制约,这也是刑事法治的题中应有之义。
根据刑诉法第79条和第80条的规定,作为最严厉的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拘留和逮捕的适用有严格的条件。特别是逮捕,针对的必须是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诸如实施新罪、危害国家安全、毁灭伪造证据、打击报复、企图自杀或逃跑等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
强制措施的种类和强度,必须要与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之间存在相当性。这是比例原则在强制措施中的具体体现。
就本案所涉嫌的损害商誉罪、谭秦东实施的具体行为及其个人情况来看,采取取保候审应已足够,并无适用逮捕的必要性。对此,上级检察院已指令凉城县检察院变更了强制措施。谭秦东被取保候审,暂获自由。
但是,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仍有意义。
可以想见,如果谭秦东从一开始就被取保候审,这个案件也不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以羁押为常态,取保为例外,这本是司法实践中长期不愈的沉疴,鸿茅药酒案再次将之暴露出来而已。
关注“跨省”,其实是模糊了视线,转移了焦点。
对本无羁押必要之人,习惯性地采取羁押措施,视比例原则如笑谈,在我看来,这才是本案中最让公众感到恐惧不安的深层原因。它与省内还是跨省无关,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权力的恣意和傲慢。
如果能以此案为契机,在这个关节点上,重申限制人身自由的比例原则,持续深入地反思警察权和检察权在羁押措施上的限度,鸿茅药酒也算对法治做出了贡献。
第三,将价值贬损的行为类推适用损害商誉罪,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
不少评论都认为,谭秦东的行为不构成损害商誉罪。理由方面,有的认为缺乏结果不法,有的认为因果关系不明,有的认为药酒成分确实对老年人不利,因而不是捏造事实等等。
再来看一遍为谭秦东惹来麻烦的这篇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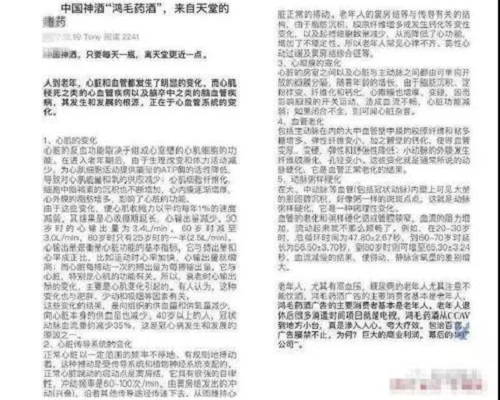
这篇文章,据谭秦东自己的说法,只有首尾两部分是他自己的文字,中间关于心肌变化、心脏传导系统、心瓣膜和血管老化等部分,都是从他处直接复制而来,系一般性的医学知识,与鸿茅药酒没有半毛钱关系。
与本案有关的,就是以下文字:
中国神酒“鸿毛药酒”,来自天堂的毒药。
中国神酒,只要每天一瓶,离天堂更近一点。
鸿毛药酒从CCAV到地方小台,真是渗入人心。夸大疗效,包治百病,广告屡禁不止,为何?巨大的商业利润,幕后的推广公司。
显然,上面几句话中,最有杀伤力的表述,是说鸿茅药酒是来自天堂的毒药。(至于说夸大疗效云云,明显不能成为入罪的理由,就没必要分析了。)
根据《刑法》第221条的规定,损害商誉罪是指“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于是,本案的关键问题是,说鸿茅药酒是来自天堂的毒药,是否符合损害商誉罪的构成要件呢?
不必急着下结论。首先要搞清楚损害商誉罪的状况。刑法对名誉的保护是碎片性的,根据主体的不同而有所区分。
对于自然人的名誉,主要是通过第246条侮辱罪和诽谤罪加以保护。“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的”,是侮辱罪;“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是诽谤罪。
既然保护法益都是自然人的名誉,两罪有何差异?侮辱,是指对他人予以轻蔑的价值贬损,至于表述内容是否真实并不重要。例如,辱骂性工作者为“婊子”的,是侮辱。
相反,诽谤,是捏造并散布某种事实,足以败坏他人名誉。所散布的事实,不足以使人信以为真的,不是诽谤,但可能属于侮辱。
例如,说某人是“猪头”或“脑子进水”。某人愤怒的理由,肯定不是因为,行为人捏造事实,虚构了“指人为猪”或“明明没水非说有水”的假话,而是因为这表述中包含价值贬损。所以,这是侮辱,不是诽谤。
在上述意义上,可以把侮辱与诽谤理解为互斥的关系,也可以说,对于那些没有捏造事实因而不能被诽谤罪包摄,但又通过价值评判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用侮辱罪加以堵截和补充。
再回过头来看损害商誉罪。侮辱罪和诽谤罪是针对自然人的一般性名誉,而损害商誉罪针对的是从事商业活动的主体(主要是公司、企业)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
针对这部分特定主体的特定名誉,刑法的保护方式,明显不同于对自然人的一般性名誉的保护。
这一点,对比第246条和第221条的构成要件表述,一望可知。
第246条在规定了“捏造事实”的诽谤罪之外,还规定了虽然没有捏造事实、但以价值贬损的方式损害他人名誉的侮辱罪,可谓对自然人的名誉实现全方位的保护。
而第221条损害商誉罪,构成要件行为仅限于“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就此而言,损害商誉罪可谓是一种针对商誉的诽谤罪,但不包括针对商誉的侮辱。
申言之,虽然损害了他人商誉,但不是通过捏造事实的方法,而是通过价值贬损的方式实施的,不构成损害商誉罪。这不仅是与第246条的侮辱罪和诽谤罪对比而出的结论,而且本来就是第221条的清晰表述。换言之,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要求。
再来看鸿茅药酒案。说鸿茅药酒是“来自天堂的毒药”,这到底是在虚构和捏造一个事实,还是在表达一种贬低性的价值评判?
“毒药”者,饮之能毙命之物。在汉语语境中,它至少有两种用法。一种是在事实陈述的意义上使用,例如,“砒霜是一种毒药”。显然,这是一种中立的说明性文字。
另一种用法,是在价值评判的层面上,将某物比喻成毒药。例如,告诫沉迷于烟酒者,可以说,“烟酒是一种毒药”。怜悯为情所苦者,又可以说,“爱情是一种毒药”,“思念是一种毒药”,甚至如那英所唱,“你的微笑,是一种毒药”。这些文字,就属于带有价值评判的意见表达了。
纵观谭文通篇,没有一处说明鸿茅药酒到底有哪些毒性成分,而且,又把它说成是“来自天堂的”毒药,这种表述方式,显然不是要引导读者在“砒霜是一种毒药”的那种陈述事实的意义上,去理解这里的“毒药”。
因此,这不是在捏造鸿茅药酒是一种毒药的事实,而是在“喝这种药酒没什么益处”的意义上,使用“毒药”这种夸张修辞的笔法,对鸿茅药酒进行一种价值贬损。
所谓“鸿茅药酒是毒药”,其实表达的是“鸿茅药酒简直就是毒药”的意思,这不是一个真假的事实判断,而是一个好坏的价值判断。
如果非要把这句话说成是捏造事实,那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指出,谭秦东捏造了鸿茅药酒的产地,事实上是内蒙古凉城,但是他竟然说是来自于天堂。
这就好比一个被骂“猪头”的人,非要通过认真地证明自己确实不是头猪,来指控对方犯了捏造事实的诽谤罪。这样的做法,可能就接近猪头了。
的确,捏造事实和价值贬损,都能损害他人商誉。但是,并非所有损害商誉的行为,都能构成刑法上的损害商誉罪。在刑法明确规定该罪的行为方式仅限于“捏造事实并散布”的情况下,如果把价值贬损的行为也纳入该罪的,那就不是依照法律规定而是根据危害性来定罪了。
而这样一种脱离法条文字、根据社会危害性进行实质判断的做法,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公然违反,它其实已经是一种类推适用了。
这,才是鸿茅药酒案在实体法上的命门所在。
第四,检方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退回补充侦查,处置方式存疑
鸿茅药酒案曝光后,检方发布通报称: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指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听取了凉城县人民检察院案件承办人的汇报,查阅了案卷材料。经研究认为,目前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指令凉城县人民检察院:将该案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并变更强制措施。
这种处置方式本属常见,不过细究起来,还是有些疑问。
根据《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相关规定,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需要查明的事项不仅包括犯罪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而且还包括“犯罪性质和罪名的认定是否正确”。
简言之,不仅要审查事实和证据,而且要审查法律适用有无错误。
在鸿茅药酒案中,犯罪嫌疑人谭秦东所实施的行为事实非常清楚,即在网上发布了一篇关于鸿茅药酒品质和性能的文章,证明这一行为的证据也没有任何疑问。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行为事实是否属于犯罪事实,即是否构成《刑法》第221条规定的损害商誉罪。
这是一个法律适用是否正确的问题,不是一个事实是否清楚或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的问题。
或有疑问认为,谭秦东的行为与重大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是一个需要证据证明的事实问题。这部分事实不清楚,为什么不能因此而退回补充侦查?回答是,对于因果关系的证明,仍然需要以谭秦东的行为,构成损害商誉罪的构成要件行为,作为前提。
换言之,如果谭秦东的行为性质不是损害商誉罪的行为,就没有必要也不应当去审查该罪中的因果关系。在损害商誉这个罪名中,构成要件行为有明确的特征描述,与构成要件结果之间相互独立,不能由结果倒推行为性质。
既然,谭秦东的行为事实本身简单清楚,也没有证据疑问,就不应当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退回补充侦查。
正如上文指出,谭秦东的行为性质是对鸿茅药酒的价值贬损而非捏造事实,指控其构成损害商誉罪,属于“犯罪性质和罪名的认定”不正确。
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犯罪事实”。根据《刑诉法》第17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司法实践中,检方不愿意直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是很常见的情形。在事实明明很清楚的情况下,有时候检察院仍然会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退回补充侦查。这是检方不愿意行使权力,把面子留给公安机关,让其自行消化。
但是,在鸿茅药酒案这样的影响性案件中,在万众瞩目的情况下,检方还是应当勇于适用法律,行使权力,否则,可能会把和稀泥、不担当、被裹挟、无制约、重结果的不良风气广而告之。
的确,最后谭秦东暂时重获了自由,有了一个不被羁押的实质结果。
但是,作为司法机关,既然出来公开表态,就不该仅仅满足于在个案中扮演排除冤情的青天大老爷,而应当趁机给公众上一堂真正的宣示法律、尊重法律的法治课。
毕竟,用“和稀泥”或者“实报实销”之类的做法解决案件,或许能够在个案中让当事人满意,平息一时的风波,但是,长远来看,从社会公众那里,恐怕是难以获得普遍的尊重和公信力的。
第五,彩蛋:为什么损害商誉罪不禁止价值贬损?
上文是对鸿茅药酒案的几点评论。接下来,咱们脱离个案,舒展一下脑筋,不妨进一步思考:对自然人的名誉保护,既有诽谤罪又有侮辱罪,但是对商家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的保护,却仅限于诽谤型的“捏造事实”,为什么?
这个问题,以往并没有人关注。我抛砖引玉,先简单地说一下个人看法。
法律文字背后,是社会现象和立法者的价值观。侵害名誉类犯罪,重点在于如何处理名誉权与言论自由这两项权利之间的冲突。
对于不同主体而言,名誉的表现形态和重要性又有不同,权利的位阶、配置和冲突解决方式,也应当有所区分。
先说个人的名誉权。
首先,如果把人格尊严放在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接受或部分接受“人是目的不是工具”的观念,那么,就会承认,每个人都应当得到他人的尊重,既不应当被捏造诬陷,也不应当被轻蔑羞辱。
其次,个人的名誉来源多元而脆弱。对普通人的一般性名誉而言,举凡品行、道德、才干、性格、感情等各个方面,都能成为外部社会评价一个人的因素,都能成为尊严和名誉受攻击被损害的对象。
与之相应,损害方式也多元化,捏造事实说他人“偷单位的办公用品”,或者价值贬损说他人“无能、爱占小便宜、窝囊废”,都可以造成一个人的名誉受损。所以,个人名誉权受伤的角度是多维的。
考虑到这些因素,刑法在事实陈述与意见发表两个维度上,全方位地保护个体的名誉不受损害。这体现在,第246条既设置了针对捏造事实的诽谤罪,又设置了针对价值贬损的侮辱罪。
不过,如所周知,言论自由是不弱于名誉权的基本权利,甚至被认为是比人格权更基础、更源初、更重要的权利。两者发生冲突时,如何配置优先性?
表面上看起来,侮辱罪和诽谤罪的规定在法律上界权很清楚,即一个人的言论自由不能以捏造事实或价值贬损的方式损害他人的名誉权,但是,这只是一般性的界权规定。
落实到个案中,特别是,在何种程度的价值贬损才能影响到社会的外部评价这一点上,此时的名誉权具体边界何在,个人的言论自由边界何在,这在具体诉讼中,需要琐细和巨大的界权成本(也可以认为是包含在广义的交易成本中)。
于是,面对这种极其广泛的个人名誉权与言论自由之间的冲突,立法者采取了一种平衡的方式。
一方面,在实体法上,侮辱罪与诽谤罪并举,在一般性规定的层面通过抽象的界权,全方位地保护个人的名誉权。
另一方面,在程序法上,又规定由被害人自己提起诉讼。这种自诉方式,实质上是把包括具体界权成本在内的打官司的交易成本,交由主张名誉权的公民个人负担。
这就是刑法对待个人名誉权的态度。那么,在商誉受损的场合呢?
首先,相对于人是目的,商品是服务于人的工具,没有那么高位阶的尊严及羞辱问题。特别是,涉及到一件商品的效用好坏,可谓见仁见智,而对商品好坏发表意见和价值评判,更是任何一个消费者的权利。
而且,对生产、销售商品的商业主体而言,商誉也不是一颗轻易就能被损害的玻璃心。
现代社会中,几乎所有的商业广告,多少都带有夸张成分,铺天盖地,无孔不入,公众对此早已习以为常。
如果商家捏造事实虚假宣传,那自然有虚假广告罪在等着他。但是,如果是在效用价值方面夸大虚饰,那么,这种价值浮夸,其实也处在现代社会能够接收和容忍的广告含义之内。
相应地,要享有多少被他人容忍商品价值浮夸的空间,自己也要能够容忍多少被价值贬损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吹牛逼还真就是要上点税的。
换句话说,既然允许商家做广告吹牛逼是“神药”,那就得允许消费者竖中指说这个是“毒药”。
对刑法来说,只要双方都没有在事实层面捏造虚构就行了。至于在价值方面的浮夸或贬损,都留给各自去忽悠吧。
在我看来,这就是《刑法》第221条损害商誉罪,只禁止“捏造事实”之诽谤,但未禁止价值贬损之侮辱的深层原因。(或许立法者也未必想得清楚,但我们可以把它挖掘出来)。
退一步来说,如果你还觉得不满意,觉得立法者偏心,对商誉保护不如个人名誉那么全面,那么,你还要看到的是,这里同样有一个整体上的保护平衡。
那就是,在程序法上,损害商誉罪是公诉案件,国家用公权力支持起诉,承担起这个交易成本。相对于侮辱罪和诽谤罪只能自己打官司来看,这也算是弥补了实体保护上缺少的那一块吧。

